新课改背景下的儿童阅读
濮阳市油田第十四小学 贾 彤
【内容摘要】
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学校中几乎每一科的知识都是通过阅读来学习的。因此,阅读能力被称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基础教育的灵魂”。但是,较高的阅读能力并不是课堂教学的结果,而是课外阅读的硕果。新课标公布十年了,儿童阅读也走过了十年路程。本文主要从新课改对课外阅读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强调是“儿童阅读”,而不是“课外阅读” ;“儿童阅读”开展实施的策略等三个方面论述儿童阅读的重要意义和行动策略,为学校、班级开展阅读提供重要的参考。
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学校中几乎每一科的知识都是通过阅读来学习的。因此,阅读能力被称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基础教育的灵魂”。但是,较高的阅读能力并不是课堂教学的结果,而是课外阅读的硕果。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到今年已经满十年了,而儿童阅读推广也已经走过了十年路程,其标志是其标志是2001年《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的出版。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老师说:“毋庸质疑的是,儿童阅读推广是在新课改的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新课程改革,颁布新的课程标准,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要完成400万字的阅读量,小学阶段要达到145万字的阅读量,儿童阅读不可能有这样蓬蓬勃勃的发展。” 那么,新课改背景下的儿童阅读到底开展得如何呢?儿童阅读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具体的阅读策略呢?这就是本文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
一、新课程改革对课外阅读的高度重视
(一)课外阅读有了“国家标准”
与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相比,新课程标准高度重视课外阅读,提出了课外阅读的总量和分量,并对课外读物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等。
1、首先是量的规定。
新课标规定: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其中,第一学段(1—2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第二学段(3—4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5—6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第四学段(7—9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
2、其次是阅读能力和习惯要求。
第一学段提出: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养成爱护图书的习惯,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第二学段提出: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
第三学段提出: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尝试进行探究性阅读,扩展自己的阅读面。第四学段提出:能利用图书馆、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和资料,帮助阅读。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
3、实施要点与评价建议。
课标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关注学生通过多种媒介的阅读,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开展各种课外阅读活动,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
修订的课标中强调:要重视学生课外阅读的评价。应根据课程标准各学段的要求,通过小组和班级交流、学习成果展示等活动,考察其阅读量、阅读面以及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4、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稻草人》《宝葫芦的秘密》等;
寓言:中国古今寓言、《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
故事:成语故事、神话故事、中外历史故事、各民族民间故事等;
诗歌散文作品:鲁迅《朝花夕拾》、冰心《繁星春水》,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等;
长篇文学名著:吴承恩《西游记》、施耐庵《水浒传》、老舍《骆驼祥子》、路遥《平凡的世界》、笛福《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名人传》、夏绿蒂·勃朗特《简·爱》、高尔基《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建议教师从中外各类优秀作品中选择推荐。
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各类历史、文化读物及传记,以及介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常识的普及性读物等,可由语文教师和各有关学科教师商议推荐。
(二)课标要求和课外阅读现状的差距
虽然新课标高度重视课外阅读,但由于更多的是从目标和宏观策略上提出建议,缺少具体可操作的方式手段,再加上长久以来,教师把教语文教材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认为教材教学是“课内教学”,课程评价、语文考试主要也是检测儿童对教材的掌握情况。儿童阅读,仍被大多数校长和教师称作“课外阅读”,不少开展课外阅读的学校能明确每周一节阅读指导课,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大人最希望孩子看的书是两类,第一类是教辅读物,第二类就是名著,而孩子最喜欢看的就是科幻的、冒险的、幽默的、童话的,所以取向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这种选择,比较功利,比较理想化,但很容易伤害孩子的阅读兴趣。
湖南师范大学的
2011年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14周岁—17周岁未成年人课外书的阅读量最大,为9.99本。其次为9周岁—13周岁未成年人,课外书阅读量为6.32本。0岁—8周岁阅读量为4.78本。3个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量均超过了成年人年图书阅读量的平均值。其中,2010年我国9周岁—13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最高,为92.1%。一方面是学生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一方面却是课标推荐的书目阅读的人数较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生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者方面的原因。但是,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课标所推荐的这些书目是否是“合适”的?也许我们除了考虑作品本身的质量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阅读的主体——儿童。
二、为什么强调是“儿童阅读”,而不是“课外阅读”
(一)儿童观与儿童阅读
儿童阅读的主体是儿童。儿童是什么?儿童是当下的存在,并非成年的预备;儿童是独立的生命,并非缩微的成人。童年应该是快乐的,幸福永远来自根部,有了快乐的童年,一生的幸福才可靠。周作人先生在《儿童文学小论》中讲过他的儿童观:不能把孩子看做是小一号的大人,以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也不能把孩子看成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动物,而应当把孩子看做独具个性的另一种人。可以说,不同的儿童观决定了不同的儿童阅读观。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童话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诞生,比西方整整晚了二三百年。而西方童话在文艺复兴之后,18世纪末,童话作为一种文体很快自觉并走向高峰。究其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成人本位”、“老者本位”的社会,社会不承认儿童独立的价格,更不会看到他们独特的精神需求,创造适合他们幻想的童话故事就更不可能了。“注意,不重视儿童独立人格不等于不重视儿童,中国人对子女历来都看得极为重要的,但子女往往是家族血脉的延续。因为期望过大,就巴不得他立即长大,于是不问儿童的身心状况和实际的接受能力,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认为最要紧的东西——纲常礼教、仕途经济之类的往儿童稚嫩的脑子灌下去,顺理成章地连带着的就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没用的东西,如游戏、想象、童话故事书等等的排斥。这样,越是对儿童重视,越使儿童失去独立人格,越使儿童远离童话和儿童文学。”(吴其南著,《中国童话发展史》)因此,在我们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并没有可靠的对儿童和童年的正确认识,也没有多少明确无疑而且经得起当代教育学和心理学检验的适合中低年级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倡导儿童读经,是与儿童生命的隔阂,只会导致死记硬背,孩子们领略不到经典的意蕴,只感受到死记硬背的痛苦。
幸运的是,儿童阅读推广十年来,无论是“亲近母语”,还是“毛虫与蝴蝶”,都在积极倡导儿童阅读,为各个年龄、不同家庭、不同心理的孩子们推荐适读的童书。而且这些童书都是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为主。阅读经典的儿童文学,儿童会得到无穷的乐趣和诗意,从而提高对母语学习的兴趣,进而在阅读中融入文化,寻找自我,确立自我。
(二)坚持儿童本位,反对功利主义阅读和轻阅读
我们倡导儿童阅读,还要反对“功利主义阅读”。调查发现:迫于升学考试压力,作文选、教辅书成为学生、家长、教师共同认定的“合法”读物;教师、家长出于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关怀,为孩子提供、推荐的诸多成人文学名著,大多沦为孩子案头的“摆设”读物;孩子间自发阅读流传的某些“畅销书”,以漫画、卡通、通俗童书为主,因常遭师长干预而成为孩子们的“地下”读物。不少家长认为看“闲书”是不务正业,恨不得孩子全身心“扎”到课本里。调查中11.8%的学生表示,因为读课外书而经常受到父母责备。
调查还显示,当前,不少中小学生阅读追求猎奇,沉醉于小说和漫画的故事情节里,课外阅读更是以娱乐、消遣类和休闲类读物为主。孩子们手中放不下来的书籍,多半是课本,是习题集、作文选,或是被视为减压玩具的动漫书、校园故事、恐怖小说……这一类阅读,真的能让孩子顺着“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步步拾级而上?
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不能让“轻阅读”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主流。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邢真说,中小学生面对“轻阅读”读物表现出异常欢愉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学生们的孩童心理——形象的画面、跌宕的情节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轻松的阅读可以缓解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休闲读物提供了追求个性、放松自我的氛围,满足了学生们获得精神慰藉的需要。但他们的阅读内容大多远离启迪思想、关注社会、思索人生等主题,对洋溢着人文主义色彩的名篇、名著缺少关注。部分学生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领略文字世界的精湛和提升精神品质,而是图消遣、寻开心,甚至少部分学生迷恋带有暴力与恐怖等情节的小说,这一现象令人担忧。一项针对上海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调查说,43%的孩子“写不出”中国和外国著名作家各一位的名字,另有5%表示知道的孩子,却填出了爱迪生、爱因斯坦、徐根宝;就是填写正确的孩子,也只是从课本上而不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了解大师之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儿童阅读应该倡导:儿童阅读那些蕴涵时代和民族精华的经典优质的书籍。但是不要一提“经典”,就想到那些“四大名著”、“安徒生童话”之类的书。童书中也有许多的经典。而且儿童阅读的内容是广泛的,不仅仅包括儿童文学的阅读,还包括儿童的科学阅读,人文阅读(历史启蒙、地理启蒙、哲学启蒙等),甚至数学阅读。就像
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薛瑞萍说:“阅读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和作文水平吗?不!阅读的能力首先是幸福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阅读的意义首先在于享受阅读的幸福和拥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儿童阅读一定要坚持儿童本位,呵护孩子幸福的童年。有些书,一个人如果不在童年时读到它们,不曾在童年时代为它们动过真情、流过眼泪,那么这个人的本性和他整个的精神成长,就可能有所欠缺,甚至将是愚昧和不文明的。
(三)“儿童阅读”把课内外阅读统合起来
传统观念认为,课内阅读指的是教科书的阅读学习,学生学习以此为主,评量测验以此为准。课外阅读则是教科书读完后行有余力,才进行的补充阅读。把课内外阅读截然划分开来,容易造成“课外阅读放任化”的局面。许多教师认为,教好教材,抓好课内教学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本义,儿童文学的阅读是课外阅读,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可抓可不抓。一定要扭转这种认识,要认识到课内外阅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反正面。吕淑湘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们经验,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看课外书。”课内学方法,课外练能力。我们一定要采取恰当地儿童阅读指导策略,实现“课外阅读课内化”,或者说“课外阅读指导化”。
目前,国内儿童阅读推广的几大力量有着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和职业,有的主要是在校园场域推广,如亲近母语、毛虫与蝴蝶项目组、萤火虫读书会;有的主要是在亲子场域推广,如红泥巴、蓝袋鼠、小书房等等。它们把学校、家庭、社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课内外阅读在他们那里没有了明显的界限。以 “毛虫与蝴蝶”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为例,他们提出:儿童阶梯阅读研究,就是为每一个儿童寻找到他此时此刻最适合的童书;在他们成长的每一个时刻,一定有着这一时刻最适宜的一本童书。这些精心挑选的书籍,将在娓娓动听的故事中,告诉他们和平、尊重、爱心、宽容、乐观、责任、合作、谦虚、诚实、朴素、自由、团结、专注、想像、宁静、勇气、敬畏、热忱、虔诚、感恩、纪律、反思……他们倡导:“晨诵、午读、暮省”的儿童阅读生活方式,这一切都将为儿童编织出一张美丽的网,呵护孩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保持着纯真、快乐与勇气。
(由于字数限制,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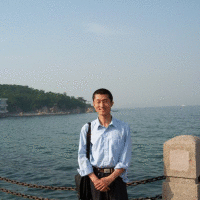



 举报
举报
 推荐
推荐 收藏
收藏
